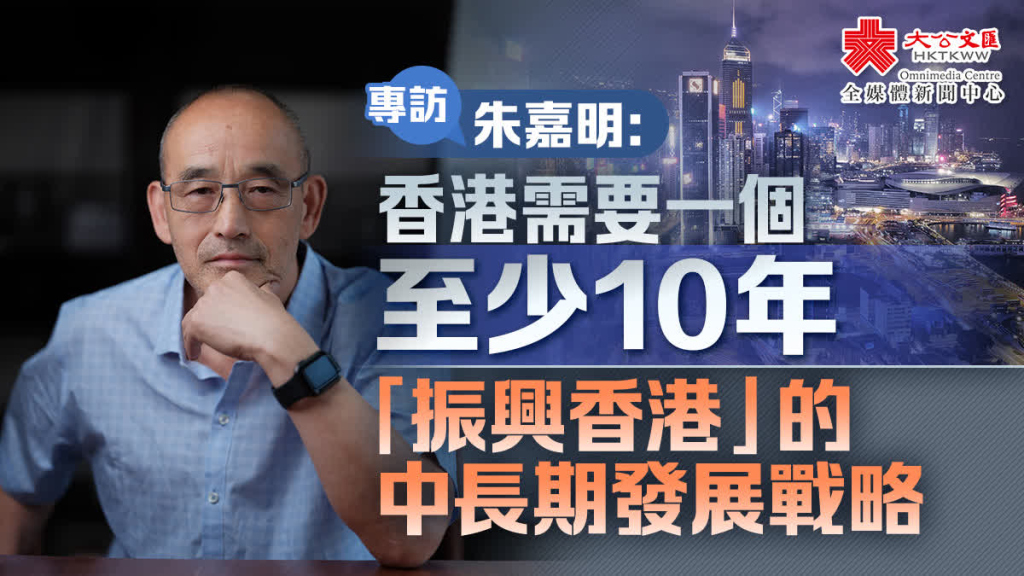
(大公文汇全媒体 记者 张安宁)一年前,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香港并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当前,香港最大的民心,就是盼望生活变得更好,盼望房子住得更宽敞一些、创业的机会更多一些、孩子的教育更好一些、年纪大了得到的照顾更好一些。要让每位市民都坚信,只要辛勤工作,就完全能够改变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一年后,疫情远去,香港社会逐步复常,经济复甦,生机再现,这一年更是香港“由治及兴”的开启之年。26周岁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值青壮年,有活力、有理想、有干劲。但香港的民生问题如何解决?发展之路要怎麽走?大公文汇全媒体记者近日专访了中国经济学家朱嘉明,请他谈谈对香港当下的民生问题与经济发展的思考。
现年73岁的朱嘉明,是中国特定的战后一代人,又是邓小平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其间,也目睹了包括冷战在内的世界风云变幻。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中国对社会变革的期待如火山喷发,力量积蓄已久,社会潮流惟以“变”字当道,政治新锐先发制人,应时而生的“改革四君子”至今仍影响中国社会进程。朱嘉明现任横琴数链数字金融研究院学术与技术委员会主席,长期关注区块链、加密数字货币、NFT、Web3.0、元宇宙等。
深圳的成功 香港功不可没
朱嘉明介绍,1985年,他先后与时任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第一副董事长唐克、深圳蛇口工业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袁庚,参加香港考察。当时,考察的课题包括“香港金融市场是否存在潜在金融危机问题”、“香港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及“招商局建立独立金融机构可行性”。考察的核心目标是解读作为“亚洲四小龙”的香港,如何为内地的改革开放发挥不可替代的贡献。从此,朱嘉明与香港结下缘分。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香港充满了生命力。朱嘉明见了政府官员、企业家、银行家、律师、著名家族成员、中资管理层成员、作家、演艺界人士,深感香港文化的多元性,其中与金庸的见面很振奋人心,两人交谈很久,朱嘉明回忆起金庸对自己的所有作品如数家珍。
彼时35岁的朱嘉明在香港认真调查研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通过那个时期的多次考察,比较深入地了解了香港以私有经济为主体,实现制造业、对外贸易和金融业紧密的发展模式。见证这里生机勃勃的同时,也发现香港存在非常严重的贫富差别,富人住在“半山”,而老百姓在居住方面尤其侷促。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内地居民与香港居民的收入水平还有巨大差距,朱嘉明已经意识到香港对内地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他表示:“历史也证明了,香港对于整个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和意义,虽然已经被很多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所认识,然而,我认为到现在为止,还是被低估的。”“中国因为有香港,才有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才有特区建设。”朱嘉明表示,中国因为有香港才有改革开放、特区建设、深圳模式。八十年代的四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其中深圳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今天举世瞩目的都市,香港功不可没。

时间再回到去年7月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中央全力支持香港积极稳妥推进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篱,充分释放香港社会蕴藏的巨大创造力和发展活力。”这亦是当下香港社会的主流共识。对此,朱嘉明也向大公文汇全媒体记者谈了他的思考。
香港民生问题的背后是恢复活力
朱嘉明表示,其实香港民生问题是一个非常表象的问题。大家都要解决民生问题,解决贫富问题,但是背后的核心问题是如何重新恢复香港的活力?让香港的经济发展不仅在大湾区,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重建雄风。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民生将是一个被动的问题。增加香港贫困阶层的社会福利,改善公屋供给,提高劳工待遇等政策,甚至实施基本收入保障制度,都是改善民生的办法,但是长久来讲,还是要解决:到底构建一个什麽样的新经济体制和结构来支持香港的发展?

他说:“周边的一些人认为可以发展Web3.0,但我认为这个想法还不够完整。在我看来,香港需要一个至少10年‘振兴香港’的中长期发展战略,这个战略不是说没人提出或者没有人思考,但是并没有一个顶层设计的大规模并以全球视野的香港经济发展战略。就民生解决民生永远解决不了,因为今天解决了民生,明天又贫困了。香港需要被政府完全照顾的人数是有限的。问题是下一步怎麽办?怎麽解决香港人才的流失和已经流失的人才的回流,这是大问题。要给所有的香港市民都能够创业的机会,这是要害。”
关于“破除利益固化藩篱”,朱嘉明表示当年香港所谓垄断问题或者利益固化的结构问题,本质上也是剥夺了香港绝大多数人能够参与创业,能够实现自己经济发展的机会。这些人本身是在那样的制度中成长起来,等他们得到机会之后,不给别人这样的机会,这条路线当然是错误的。他提到,当年的利益固化是一个非常複杂的历史过程,所以有政府公务员,甚至有高级公务员捲入到丑闻里,相关的经验教训还是要继续总结;只关心民生,是不能够解决香港一代一代的人,特别是现在年轻人的创业和就业机会,这是重中之重。
香港更需要顶层设计 将经济民生问题同中长期发展战略相结合
朱嘉明总结研究香港经济发展的历史时说道,要找到它的局限性,香港现在自由选择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更需要一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把香港眼前面临的经济问题、民生问题,和中长期的发展战略结合在一起。
朱嘉明说:“香港需要一个10年甚至20年的振奋人心、符合实际的规划。以后的各届特首,在这个规划下把香港一步一步恢复起来,这是一个长期的、认真的工作,在规划中去寻找民生的位置和民生的规模。”
谈到香港目前的四个方向:金融中心、科技中心、贸易物流供应链中心、固定资产资源中心,朱嘉明分别进行了分析。
第一,关于香港发展科技,朱嘉明认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为什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数码港的想法是对的,但失败了。1991年,我是支持香港创立科技大学的,成立大会我在现场。然而,香港高科技没有因为建造这个学校而解决科技人才短缺的问题。这是因为,香港至今没有从根本上构建支持高科技发展的教育体系和吸纳人才的制度。非但如此,香港自己培养的人才,持续发生反向流失。”他提到,历届香港特首都在一定程度上懂得经济、法律、政务、房地产、国际贸易和金融,但是对高科技的训练不足。香港已经错失了成为高科技发展基地的一个历史时期。
第二,香港继续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朱嘉明表示现在比较複杂,因为一个金融中心需要自由竞争的经济制度来支撑。现在受客观或者主观因素的限制,能不能和新加坡竞争,或者是和上海竞争,有它的先发优势,也有近年来形成的劣势,这问题是可以研究的,不是没有馀地。
第三,香港继续成为全球供应链或者贸易中心?朱嘉明认为,现在也很难。“因为香港的这个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中国本身在世界供应链的位置也在调整,更何况香港做传统加工工业,过去几十年已经过去了,已经回不来了。”
第四,振兴传统房地产行业?他认为,这条道路基本不存在前途。香港是世界少有的房地产过度开放的地方。其负面后果,还要经过较长时间得以化解。
建议香港成立“香港发展振兴综合研究院” 重新确定香港在国际竞争中的定位
朱嘉明建议,香港应该尽快着手成立一个有经济学家、科学家、官员参与的,由中央政府支持的“香港发展振兴综合研究院”。如果这样的研究院成立了,需要立即制定香港中期(五至十年)的科技政策、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
关于重新确定香港在国际竞争中的定位,朱嘉明提出:将前沿科学和科技金融结合,推动香港成为以“前沿科学”为基础,以“实体经济”为支撑,以“大湾区”为腹地,以东南亚为辐射圈的“科技金融”中心。这个“中心”的核心特徵是将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科技与金融产业融合,超越传统的“科技金融化”和“金融科技化”。一方面,香港可以从这个中心受益,另一方面,这个中心对周边地区会产生“溢出”效应。
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这样的“中心”尚无先例,朱嘉明认为,这是时代的需求,也是再“全球化”的需求。同时,更是一个创造性的系统工程。
“比如科学问题,关于‘大科学’,我们关注差不多八个科学前沿,香港能解决一个两个也可以。每天全世界那麽多人分析火星,现在大家既要上宇宙空间又要下深海。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香港政府需要给民众一个perspective,一个愿景,然后鼓舞大家。”他指出,确定香港在大湾区、整个亚太地区的位置,让大家重新觉得I am proud of Hong Kong。只有这样,分布在全球的那麽多优秀的香港人,可以回来。综合而言,要推动和刺激流失的精英和优秀人才的回流。

他特别提到,香港在发展科技金融、科技艺术领域,具有极大的空间。现在,人工智能技术如火如荼,香港也是有机会的,香港可以成为人工智能和金融和艺术结合的试验场和高地。这样的目标,不是仅靠政府可以规划实现的,但是,政府要提供一个代表未来的全新的生态环境。有了这样的生态环境,青年人的潜力就会爆发出来。
谈到“发展优先”时,朱嘉明认为要客观公正地回顾和总结历史。以前在总结历史上,大家会有很多分歧,现在求同存异,关于“向前发展”大家总是能够形成共识的,“发展优先”压倒一切。只有通过可持续发展实现繁荣,才有可能解决民生问题。
最后,朱嘉明告诉大公文汇全媒体记者:“香港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是巨大的。现在香港需要信心、战略目标、实事求是的规划。距离我第一次去香港,很快就四十年了,我关心香港,祝福香港,也相信香港能够再次振兴!”

